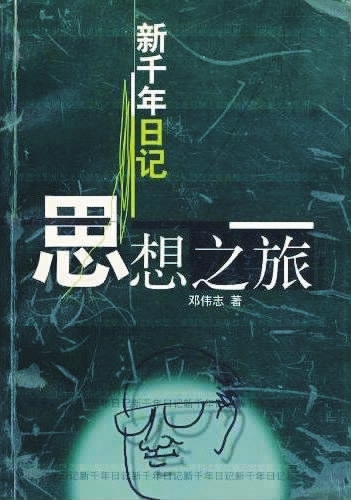这些年,“邓伟志”的大名我是熟知的,有幸读过他的文章,听过他的发言。他是上海大学知名教授,也曾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。在文庙淘书,我欣然买到他的“新千年日记”《思想之旅》。
书是作者2000年的日记集结,按地点逐日编排,一些日记的后面还附录了他写的文章,可视之为日记的补充。这一年,他两次出国讲学,历时两个多月,我读了这段时间的日记,仿佛分文未掏,跟着他走了好几个国家。而国内,他也奔波多地。这些扑面而来的所见所闻所思,开我眼界,启我心扉。
思想,那是属于我们每个个体的,不同于流俗的。思想是在高处,俯瞰现实,做出评点,热中有冷,冷中有热。一个人没有思想,只不过是徒有躯壳。思想含有理性,犹如花茎上的果实;思想含有识见,犹如冥暗中闪现火花;思想含有智慧,犹如炼钢经过冷却淬火而成。读到妙处、精彩之处,忍不住我会用笔划下来,暗暗叫好,庆幸出版社为我们这个时代保存了这个有意义、有价值的文本。他随时随地注意观察,所发议论针砭时事,精到实在,发人深省。这恐怕不仅仅是出于他的职业敏感吧,他是从骨子里喜欢思想的哲人,因而表达得很真切、很真挚,也很感人。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”,这是魏征所说。我想,今天社会应该有更多宽容,正因为听到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声音,才能有更多的参照,从而集思广益,共同推动时代进步。
思想,须有思想者的清明。流动的水不会腐浊,与时俱进的思想不会僵化、枯滞。作者的可贵,就在于他向前看,视野宽广,善于用历史的、发展的眼光洞察事物,因而理念比较新,不受拘囿,且有穿透力。比如,他说,“既然‘环球同此凉热’,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露出曙光,科技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化还会远吗?”关于同与异,它们会产生碰撞,“‘新同’之中有‘新异’;新异之后又会有更新的同。‘同’与‘异’的互动,推动着地球的自转与公转,推动着世界的一体与多样。”然而,东西有融合,也有冲撞,中国不可能走西化的路。理论是民族的灵魂,没有攻不破的“禁区”,但“迷信是创新的牢笼。”“十大预测”中,许多政府职能将转移给社会,城市化速度加快、城乡差距缩小,教育将实现多媒体化、全球化,居民、村民将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,生产时间缩短、休闲时间增多,不正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所努力的吗?
他是入世的,他的思想触发于现实,感应于现实,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激发他发现问题,决不留情面。他从江西一位因贪污、受贿落马的副省长先前四处题招牌、后又不得不组织人铲除的现象引发思索,认为“为了避免铲与刮的历史重演,题字还是请书法家为好。”他从成克杰贪污早有时日,仍受到重用,看出“荒唐的体制才是腐败的温床。”他观察世态,“青少年的那个不纯洁的一面,说穿了,是从中老年那里学来的,是受中老年的传染、污染。”他去奥地利考察,从平民居住的“马克思屋”得到启示,人家“高干”们也愿意与民同住,他们有公仆意识,我们是不是要加个“更”字呢?中高级干部是不是也应该分散住在百姓当中呢?如此,不视察胜于视察。在意大利的威尼斯,路经马可·波罗故居,生发出如果今天能多出几个马可·波罗,如实地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实况,中国申报奥运会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不必费那么多周折的念头。走访欧洲一路,在佛罗伦萨,他在想:当代中国的但丁在哪里?中国怎样才能出但丁,出《神曲》?在他看来,《玩偶之家》就是妇女社会学的一个案例,一部社会问题剧,易卜生属于不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;韦伯死后大有名气,也说明了人们对一种学说的认识过程很复杂,有时越是超前的东西,越不易被当时的人所接受。又说“人家是从学术上研究马克思,而我们多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棍子,”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谈何容易,故有的提法宜谨慎。谈到理论创新,“要防止学术市场化,学者官僚化。要有点李白‘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’的精神。”实施社会监督,“不要老是拿‘社会影响’当顶门杠。”在南京参观古城墙,让他联想到,“城墙就在脚下,人民才是城墙,脱离人民是站不住的啊!”
对婚姻、家庭的研究,许多见解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理解和透彻的思考。面临婚姻法修改,他推荐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,认为“这本书比当前开放的观念还开放”,“有些自以为超前的人,其实并不超前,比恩格斯差远哩!落后得很呐!”他强调恩格斯婚姻观的基本点:1.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;2.只有继续保持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;3.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。他提出对“第三者”现象要作具体分析,当年瞿秋白爱上的也是有夫之妇,认为有爱情,不会离婚;爱情有修补的可能,不要草率地离婚;实在是没有了爱情,应迅速离婚。从历史大趋势上看,无错离婚是社会的进步。
有对负面的尖锐批评,就有对正面的热烈赞扬。他张扬人的尊严和健康的人格,以及坚持真理的信念和宁折不弯的品格,这和鲁迅“立人”的主张是一致的。参观古罗马遗址,他写下“什么都没有了,柱子还直立在那里,几千年不动摇,真够坚定的。历史需要柱子精神。人应该有柱子精神。”他称赞“石头可碎不可弯”,这成为他说话为文有棱角的动力。
他爱读书报,从书中汲取思想,并在日记中勇于反思自己,加以鞭策。如,边读陈寅恪的书,边想陈寅恪怎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?他在想:我在62岁以前没走“陈寅恪之路”,容不容我62岁以后走一条“陈寅恪之路”?对世事他看得透彻,日记中有很多称得上明白话,比如,从沧桑巨变,领悟“天下哪有永恒的东西?”他敢于打破“个人崇拜”的偶像,揭示了人的局限和困窘。看到国外媒体报道,如某某是“中国最有权和最有钱的后代”,某某的手稿又超过了谁,心中发痛。
叶圣陶先生有言:“日记材料是个人每天的见闻、行为以及感想,包括起来说,就是整个生活。我们写日记,写作这件事就跟生活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。从这种联系逐渐发展,以至著书立说,述作等身,总不会违反现实,或者取那种不真诚不严肃的态度。”日记贵在有思想,贵在有真实性,不粉饰,不逃避,对万事万物不背过脸。对作者而言,日记的本真,来源于人格的坦荡,来源于精神的豁达,来源于对事物的真知。作者有“思想界的男子汉”之称,过去主攻家庭社会学,知识社会学,近年主攻城市社会学。此外,在自然科学方面,也写过两本书,在文学方面,出版过《我就是我》等数本杂文集,先后在二十余家报刊办杂文专栏,曾获林放杂文奖,人民日报金台奖。所以,不难理解他的日记有较深厚的思想、文化底蕴。从日记的文字来看,亦注意生活化语言的运用,以显生动活泼,形象、幽默、风趣的表达随处可见。